厦门,十月.
空气里还是那股子挥之不去的咸湿味,黏糊糊的,像极了当年在维多利亚港边吹过的风.

我把手里的喜茶杯子捏扁了,扔进垃圾桶,发出“噗”的一声闷响.
周围全是人,挤得慌.
今晚的会展中心有灯光秀,不知道是为了庆祝什么,反正这年头,庆祝什么都需要理由,又不完全需要理由.
我站在环岛路的一处栈道上,看着前面乌压压的人头,突然有点想笑.
大概是想起张爱玲说过,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现在的场面,袍子够华美了,光怪陆离的,这虱子嘛,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凑热闹的闲人.
其实我不爱凑热闹,真的.
在纽约那几年,每逢Thanksgiving或者New York Eve,时代广场落球的时候,我都是躲在布鲁克林的小公寓里,煮一壶热红酒,看伍迪·艾伦的老片子.
那时候觉得孤独是种格调,是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
现在呢,回国这几年,在上海的梧桐树下走过,在香港的中环天桥上挤过,慢慢觉得,孤独就是孤独,没什么好装的.
它就像一颗放久了的水果糖,看着还是那个鲜艳的包装纸,剥开来,里面已经化了一半,粘手,还有点齁嗓子.
今晚的风有点大,吹得我裙角乱飞.
我拢了拢头发,视线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游走.
灯光秀开始了.
巨大的光束像利剑一样刺破夜空,把云层染成了诡异的紫红色.
人群发出整齐划一的“哇”声,手机屏幕亮成了一片星海.
就在那一瞬间,那道紫色的光扫过人群边缘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背影.
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像是被谁狠狠攥了一把.
那件灰色的风衣,肩膀微微有点塌,走路的时候习惯性地把右手插在口袋里,左手拿着手机,头微微低着.
太像了.
像到我几乎要脱口而出那个名字.
那个在波士顿的大雪天里,陪我走了五条街去买一盒大白兔奶糖的人.

那时候我们都穷,穷得只剩下梦想和爱情.
他说,等以后回国了,要在上海买个大房子,落地窗要正对着黄浦江,每天早上醒来就能看到船只穿梭.
我笑他俗气,他说这叫入世.
后来呢?
后来就像所有俗套的都市爱情故事一样,我们在现实的洪流里走散了.
他在陆家嘴的高楼里加班到深夜,我在soho的格子间里改稿改到崩溃.
那个背影在人群里若隐若现,像个幽灵.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脚下的木栈道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混杂在喧闹的人声里,听得人心里发慌.
我居然有点怕.
怕追上他,发现不是他;更怕追上他,发现真的是他.
如果是他,我该说什么?
“嗨,好久不见”?还是“你也来看灯光秀”?
太矫情了.
或许就像《半生缘》里曼桢说的,“我们回不去了”.
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歪歪扭扭地投射在地面上,像是一条条纠缠不清的蛇.
我跟着那个背影,穿过了一群举着荧光棒的小孩,绕过了一对正在自拍的情侣.
那对情侣笑得很甜,女孩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红彤彤的,在灯光下泛着油光.
我想起以前,他也给我买过糖葫芦.
那是北京的冬天,后海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脸.
他把糖葫芦最上面的那颗山楂咬掉一半,把核吐出来,然后把剩下的递给我,说:“没核了,吃吧”.
那时候觉得这就是天长地久了.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傻,傻得可爱,也傻得让人心疼.

前面的背影突然停住了.
他站在栏杆边,面向大海,似乎在看什么.
我也停下了脚步,隔着大概五六米的距离,看着他.
海浪拍打着礁石,哗啦,哗啦.
这声音听久了,有点像某种古老的催眠曲.
我突然想起以前写过的一句话:记忆是某种形式的谋杀,它杀死了当下的快乐,只留下一具名为“怀念”的尸体.
此时此刻,我就是那个守着尸体的人.
那个男人转过身来了.
借着路灯昏黄的光,我看清了他的脸.
陌生的眉眼,陌生的神情,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
不是他.
那一瞬间,说不上是失望还是庆幸.
就像是悬在半空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虽然砸到了脚,有点疼,但好歹是踏实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转身往回走.
海风似乎更大了,吹得眼睛有点酸涩.
其实早就该明白的,有些人,有些事,就像这海边的沙堡,潮水一上来,就什么都没了.
不管是上海的黄浦江,还是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或者是这厦门的环岛路.
水都是一样的水,流动的,无情的,带走一切的.
我从包里摸出一颗薄荷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
辛辣的凉意瞬间冲上脑门,让人清醒了不少.
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了.
那个在大雪天买奶糖的男孩,那个在后海挑山楂核的男人,都已经死在了过去的时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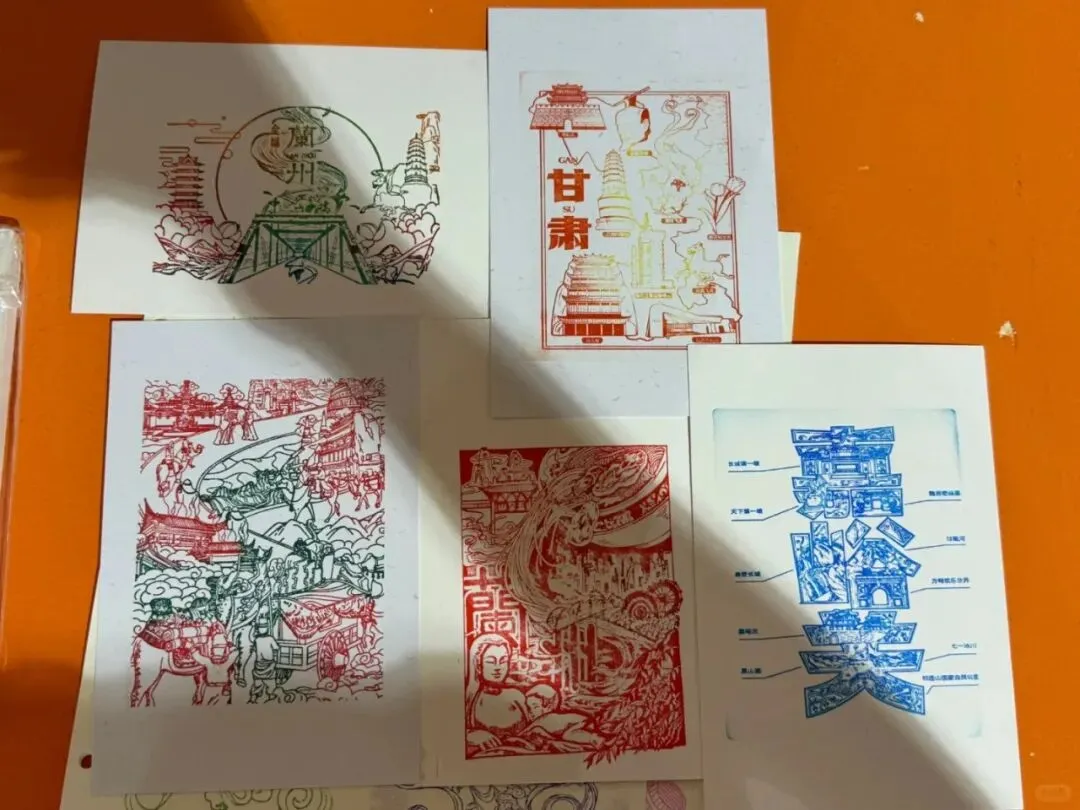
现在的我,是一个靠码字为生的中年女人,会为了稿费斤斤计较,会为了眼角的细纹焦虑,也会在某个瞬间,因为一个相似的背影而心神不宁.
这就叫生活吧.
灯光秀还在继续,五颜六色的光柱在夜空中交织,变幻出各种图案.
海豚,白鹭,钢琴,还有巨大的“我爱厦门”字样.
人群依然在欢呼,在拍照,在努力记录下这一刻的美好.
我找了个长椅坐下,看着远处漆黑的海面.
海的那边是什么呢?
可能是金门,可能是台湾,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就是无尽的黑暗.
就像我们的未来,谁也看不清.
但我知道,明天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
我还是会打开电脑,敲下一个个方块字,去构建一个个虚幻的世界.
而在那些世界里,或许会有那么一对恋人.
他们在波士顿的大雪里紧紧相拥,在上海的落地窗前看日出,一直一直走下去,直到白头.
那是我的救赎,也是我的妥协.
起风了.
该回家了.
我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陌生的背影.
他在抽烟,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祝你幸福,陌生人.
也祝那个记忆里的他,在平行时空里,一切安好.
至于我,我有这漫天的星光,还有这一口袋的薄荷糖,这就够了.
真的,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