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世界传播精彩中国
Spread Wonderful China to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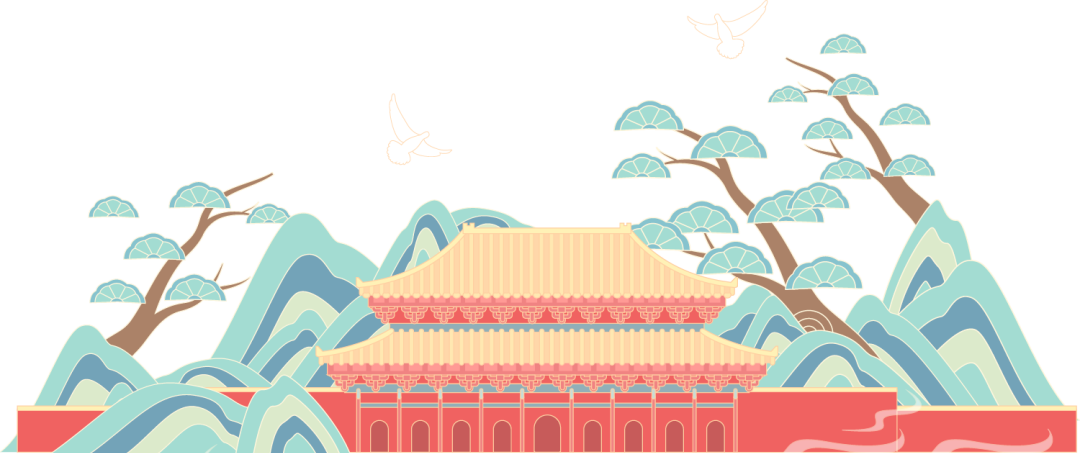
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叙事:作用机制与实践策略
国际传播是基于话语实践的认同建构,说服是其最终目的。叙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说服方式,能够使受众沉浸在一个整合了注意、情感和意象的独特心理过程中。它通过叙事理解、注意力集中、情绪经历和叙事呈现,让受众全身心投入到事先营造的故事场景中,经历并感知故事的情节与情感,获得近乎真实的临场体验,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态度与认知。在整个过程中,叙事理解是进入故事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改变态度的前提和基础。但在文化差异悬殊的国际传播语境下,叙事理解难免存在一定的折扣与偏差,而能够有效弥合这一缺陷,架构起跨越文化差异的沟通桥梁的便是共情叙事。
一、共情与共情叙事
互联网的发展和全球传媒技术的变革催生了国际传播的情感转向,共情叙事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实践路径,其有效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检验。但在理论层面,共情叙事何以成为国际传播过程中认知建构的重要手段,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又是怎样的,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挖掘。要理清这些问题,首先要理解共情。
(一)共情
尽管学界对共情的定义一直争论不休,但共情包含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成分已成为普遍共识。情感共情(Emotional Empathy)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受和体验。已有研究表明,人体内的镜像神经元能够读取他人的情绪,并激发相关脑区,将他人的情感表征转化成自身的情感表征,从而对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因而,情感共情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应过程。人们常说的“共情是一种本能”,指的就是情感共情的反应机理。它并非人类所特有,部分动物也具有情感共情的能力。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是识别他人情绪,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它侧重于对他人情感的推测和判断,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观点采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调节过程。相较于情感共情,认知共情需要更多意识成分的参与,以及更复杂的脑反应。
认知神经学的研究已经证明,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所用到的脑区是不同的。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研究发现,一岁左右的婴儿与认知相关的脑区还没有发育完备,但已经能够对哭泣等情绪做出相同或相似的情感反应。而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则发现,患者在情感共情能力受损的情况下,认知共情能力不受影响。这也再次验证了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的独立性。
共情认知成分的发现,一方面证实了共情中含有理性的成分,情感不等于情绪化,更不是违背理性,从而有力回击了“情感即非理性”的论断;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共情实际上是建立在自身认知基础之上的主观体验,而当前的认知是由过去的知识和经验所决定的。因此,共情的实现意味着与旧有认知的碰撞与融合,即说服效果的初步达成。
二、基于共情叙事的国际传播作用机制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既往国际传播实践中,还存在缺乏自我叙事能力,过于刻板生硬等问题。共情叙事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理论工具,不仅可以创新我国的对外传播方式,也为本土化理论谱系的搭建和探索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共情叙事何以在国际传播中完成说服使命,发挥致效机理,大致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一)吸引注意:跨越文化差异,抢占注意力资源
国际传播是话语竞争,而话语竞争首要的是吸引目标受众的注意力。当下,智能媒体终端的普及和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信息过载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在海量信息的轰炸下,碎片化的阅读和浅思考取代了纸媒时代的系统阅读和深度思考,追求新鲜刺激的瞬时体验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与此同时,无限的信息反衬出个体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对受众注意力的争夺成为国际传播制胜的关键。在这样的背景下,共情叙事以其轻松跨越文化差异,快速凝聚受众注意力的能力,成为国际传播语境下撬动认知的有效策略。
(二)唤起共鸣:诉诸高位价值,诱发共同情感
凝聚共识、唤起共鸣是建立信任、实现说服的重要步骤,而共情元素在其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共情叙事通过使受众沉浸于故事中,与现实世界发生暂时的“隔离”。这种“隔离”具体表现为物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物理层面即对周遭环境及所发生的事情不敏感;心理层面即不易察觉故事与现实的差距。在国际传播情境下,“隔离”则表现为受众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差异的忽略,并暂时将自我及他者的政治立场归属等置于一旁。在这种“隔离”之下,受众的情感与认知高度参与到故事情节之中,同时形成情感投射与认知塑造。随着故事的推进,受众的自我意识逐渐削弱,与角色融为一体。情感上,经历强烈的共情体验;认知上,将对角色的喜爱和认同转化为对其价值观和行为的认同,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行为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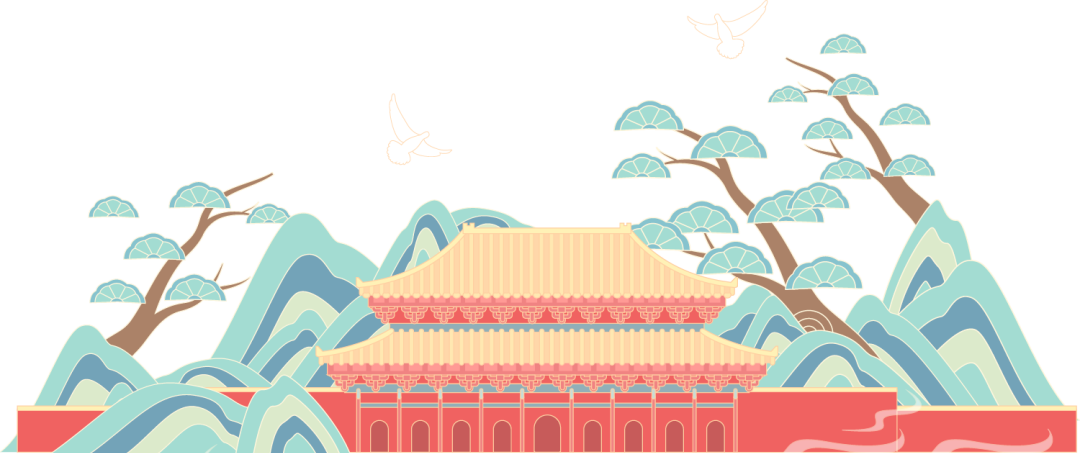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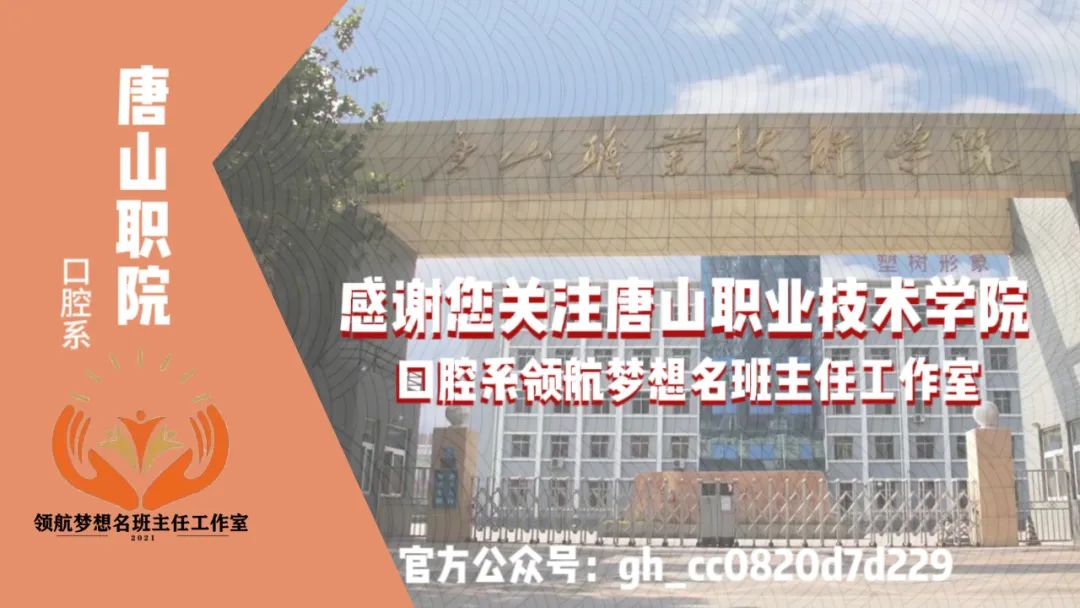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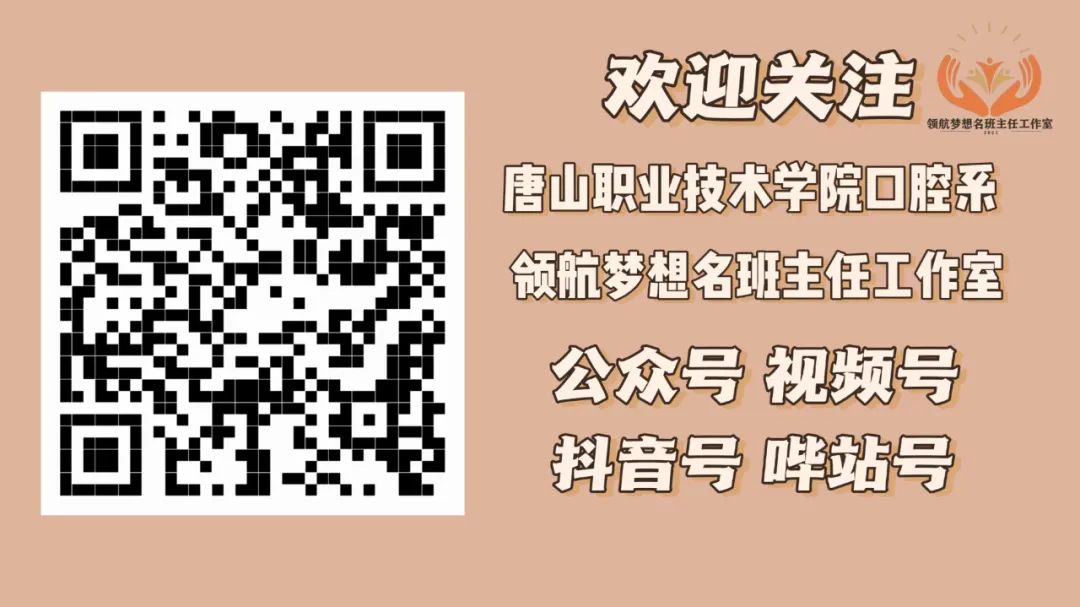
来源:“学习强国”
责任编辑:李雅倩
指导审核:胥佳利
出品: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口腔系领航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