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从纽约飞回上海,落地浦东的时候,雨下得正紧.

也是这样一个湿漉漉的傍晚,我在厦门.
环岛路上的风很大,吹得人发丝凌乱,我裹紧了那件在香港中环买的薄风衣,却依然挡不住海风里那股咸涩的凉意.
眼前是那个巨大的、像金元宝一样的建筑——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听说这里办过金砖会议,那是何等的光耀与喧腾,各国政要云集,镁光灯闪烁如昼.
可此刻,它静默地伫立在夜色里,像个退了休的老戏骨,独自品味着散场后的落寞.
我手里捏着半颗早就化了的大白兔奶糖,那是刚才在路边小店随手买的.
糖纸黏糊糊的,粘在指尖上,像极了那些甩不掉的、黏稠的往事.
这几年,日子过得像过山车.
从曼哈顿的落地窗前俯瞰中央公园的秋色,到如今在这座南方海岛的边缘徘徊,中间隔着的,不仅仅是太平洋,更是几段断裂的人生.
我记得张爱玲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那时候觉得这话矫情,现在想想,真是一针见血.
我们都在努力维持着那袭袍子的光鲜,却只有自己知道,里面的虱子咬得有多疼.
沿着会展中心外围走,路灯昏黄,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又在转角处折断.
这光影,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上海弄堂里,透过彩色玻璃窗看出去的世界,也是这样斑驳陆离,带着点不真实的梦幻感.
那时候手里若是有一块大白兔,那就是天大的快乐,能甜上一整天.
现在的糖,怎么吃都带着一股子工业糖精的味儿,甜得发腻,却甜不到心里去.
或许不是糖变了,是吃糖的人心境变了.
路过那个著名的金砖会议标志性雕塑,在夜色下泛着冷冷的金属光泽.
它见证过历史的宏大叙事,见证过大国之间的博弈与握手.
而我,只是个渺小的过客,带着一身疲惫和满心的疮痍,路过它的辉煌.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没来由地想笑.
就像伍尔夫笔下的达洛维夫人,在买花的那个清晨,那一瞬间的欢愉与整个伦敦的喧嚣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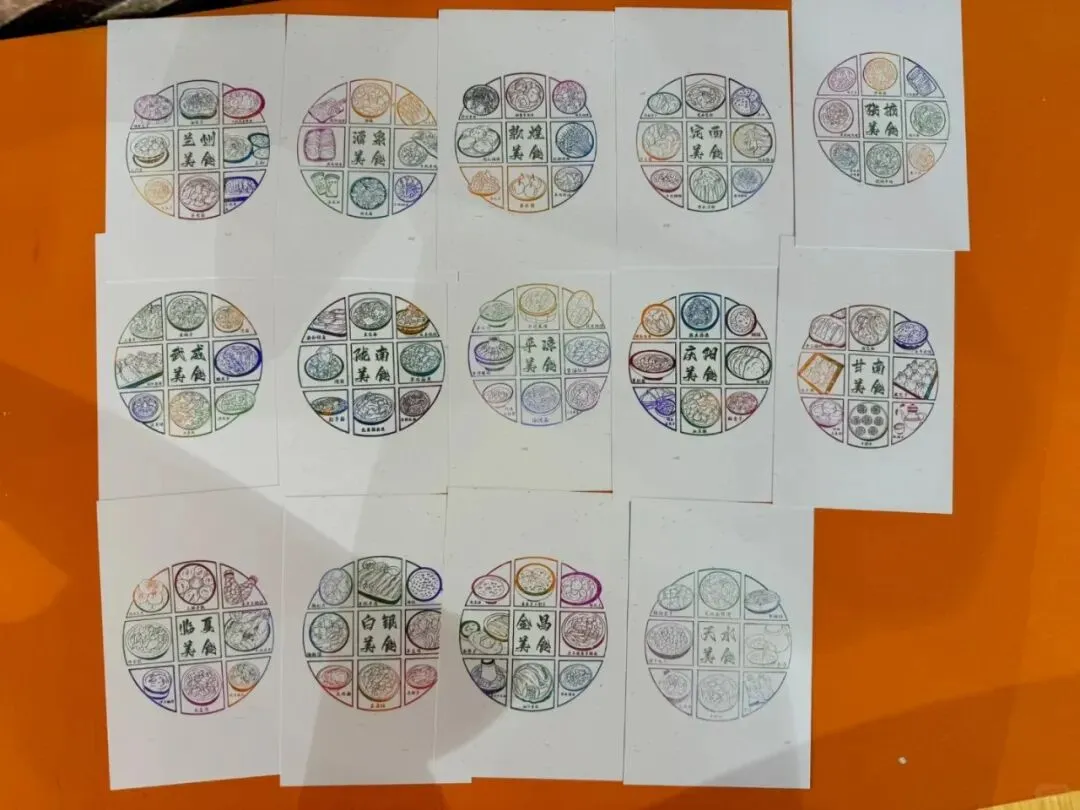
我的落魄,与这里的宏大,竟也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前阵子在香港,为了那个版权纠纷的案子,几乎耗尽了心力.
坐在维港边的咖啡馆里,看着对岸的灯火璀璨,只觉得那繁华是别人的,与我无关.
那时候想,要是能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好了.
于是我就来了厦门.
以为这里只有鼓浪屿的小资和曾厝垵的热闹,没想到,在会展中心这片空旷地带,我找到了另一种共鸣.
这里有一种“盛宴之后”的空寂.
就像一个盛装打扮的舞女,卸了妆,坐在后台的角落里抽烟.
那种疲惫,那种松弛,那种“爱谁谁”的颓废感,竟然让我感到莫名的安心.
海风里夹杂着淡淡的腥味,还有不知从哪飘来的桂花香,很淡,若有若无.
这味道让我想起在波士顿读书时的那个深秋,查尔斯河畔也是这样的风,也是这样的心境.
那时候是为了论文发愁,现在是为了生计奔波.
时间是个拙劣的魔术师,换了布景,换了道具,却没换掉那个焦虑的主角.
我走到海边的栈道上,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哗啦——哗啦——
像是某种古老的咒语,一遍遍地冲刷着心里的泥沙.
我想起那天在清名桥下,也是听着这样的水声.
那是江南的柔波,细腻温吞;而这里是大海的呼吸,粗粝豪放.
但本质上,水都是一样的.
它们容纳一切,无论是金砖会议的辉煌,还是我这样一个中年女人的失意.
水不问来路,也不问归途,只是流淌,只是存在.
我把那颗化了一半的大白兔塞进嘴里.

甜味在舌尖炸开,那种久违的、单纯的甜,让我鼻子一酸.
其实,生活也就这样吧.
有过高光时刻,自然也会有至暗时刻.
就像这会展中心,它不可能永远灯火通明,永远宾客盈门.
它也需要这样的夜晚,独自面对大海,面对黑暗,面对真实的自己.
而我,也不过是在经历人生的一段“休整期”.
那个在上海写专栏意气风发的我,那个在纽约街头谈笑风生的我,和现在这个在厦门海边吹冷风的我,都是我.
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狼狈.
都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远处,一艘轮船拉响了汽笛,声音低沉悠长,穿透了夜幕.
那或许是归航的信号,也或许是出发的号角.
谁知道呢.
我裹紧风衣,转身往回走.
路灯似乎比刚才亮了一些,把前路照得稍微清晰了点.
我想,回去该写点什么了.
不写那些宏大的叙事,不写那些虚伪的繁华.
就写这晚风,这路灯,这化掉的奶糖,还有这颗在落魄中依然跳动的心.
毕竟,文字是我的救赎,也是我最后的堡垒.
只要还能写,我就没有输.
就像这会展中心,哪怕此刻寂静无声,谁又能说它不再雄伟呢.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我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