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从纽约回上海,行李箱里塞满了书,心里却空荡荡的. 现在站在厦门的会展中心前,海风大得惊人,几乎要掀翻我的帽子. 头发乱了,像是某种隐喻,心绪也跟着乱糟糟地缠绕在一起. 这里不像维多利亚港,那边的海风带着铜臭味和香水味,这里的风,咸湿,粗粝,更像是一种没经过修饰的质问.
我手里攥着一颗大白兔奶糖,是刚才在便利店随手买的. 剥开那层薄薄的糯米纸,有些化了,黏在指尖上,像极了某些甩不掉的陈年旧事. 记得在波士顿的冬天,我也常买这种糖,为了那一点点虚妄的甜,去对抗窗外漫长的暴风雪. 那时候觉得时间很慢,慢到可以听见雪落在松针上的声音. 现在觉得时间太快,快到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有些人就已经变成了通讯录里一个灰色的头像.
会展中心的建筑线条很硬,但在夜色里,被那些暖黄色的路灯柔化了. 光影斑驳地投在地上,像是一张张没冲洗好的旧底片. 我沿着那条长长的海岸线走,听见浪拍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在数着什么. 可能是在数我们错过的那些日子吧. 张爱玲说,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 以前读不懂,觉得太苍凉. 现在懂了,却不敢深想.

路边有个卖荧光棒的小贩,手里拿着一把发光的东西,在黑夜里挥舞. 那光亮很微弱,但在巨大的海风面前,显得特别倔强. 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弄堂里玩过的玻璃弹珠,里面藏着彩色的花纹,对着太阳看,就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那个小贩,守着自己的一点点光,以为能照亮整片海. 其实,海根本不在乎.
走累了,我在石阶上坐下. 海水是黑色的,深不见底,像某种巨大的、沉默的兽. 远处有星星点点的渔火,或者是船灯,晃晃悠悠的. 这种摇晃感让我有些眩晕,仿佛回到了那年从香港坐天星小轮去尖沙咀. 也是这样的夜,也是这样的水声. 那时候身边还有人陪着,说着不着边际的话,讨论伍尔夫的意识流到底是不是一种逃避.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这片陌生又熟悉的海.
忽然觉得有点冷,拉紧了风衣领口. 这种冷不是物理上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带着点湿气. 就像那些被我们刻意压在箱底的记忆,平时不觉得,一遇到阴雨天,就开始隐隐作痛. 我把那颗大白兔放进嘴里,甜味瞬间在舌尖炸开. 太甜了,甜得有点发腻,甚至带出了一点点苦味. 生活大概也是这样吧,所有的甜美背后,都藏着不易察觉的代价.

旁边走过一对情侣,女孩手里拿着一串气球,笑声很脆,被风吹得很远. 我看着他们,没有羡慕,只有一种淡淡的慈悲. 年轻真好啊,还可以肆无忌惮地笑,还可以相信永远. 而我们这些“过来人”,早就学会了在风起的时候,先护住自己的烛火.
我想起昨晚在酒店读的木心,他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其实慢的不是日色,是我们的心. 现在我们的心太急了,急着赶路,急着成功,急着去爱,又急着遗忘. 就像这会展中心的海风,急匆匆地来,又急匆匆地走,什么都带不走,只留下一地凌乱.
或许,我不该来这里. 或者说,我不该一个人来这里. 独处的时候,人总是容易变得脆弱,容易被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击中. 比如一块融化的糖,比如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比如远处那盏忽明忽暗的灯. 它们都在提醒我,有些东西,真的已经回不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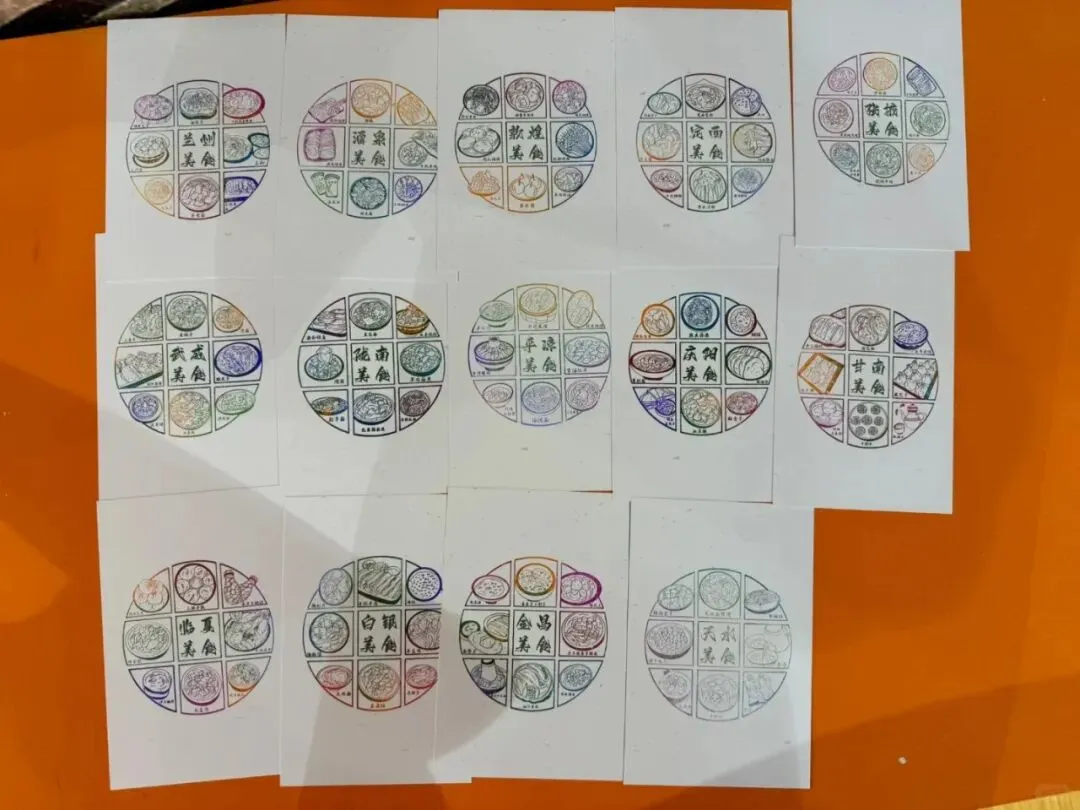
但我又庆幸自己来了. 在这个风很大的夜晚,我终于可以不用伪装,不用端着架子做一个体面的成年人. 我可以任由头发乱着,任由眼妆晕开,任由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在脑海里横冲直撞. 这是一种奢侈的自由.
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那颗糖已经吃完了. 嘴里还留着一点点奶香,混杂着海风的咸味. 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吧,复杂,难以言说,却又真实得让人想哭. 我看着远处的大海,心里默默说了一句:算了. 对过去算了,对遗憾算了,对那些没能完成的约定,也算了.
风还在吹,但我该回去了. 明天还要赶早班机,还要回到那个充满秩序和规则的世界里去. 但在这一刻,在这片漆黑的海边,我是属于我自己的. 哪怕只有一瞬间.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