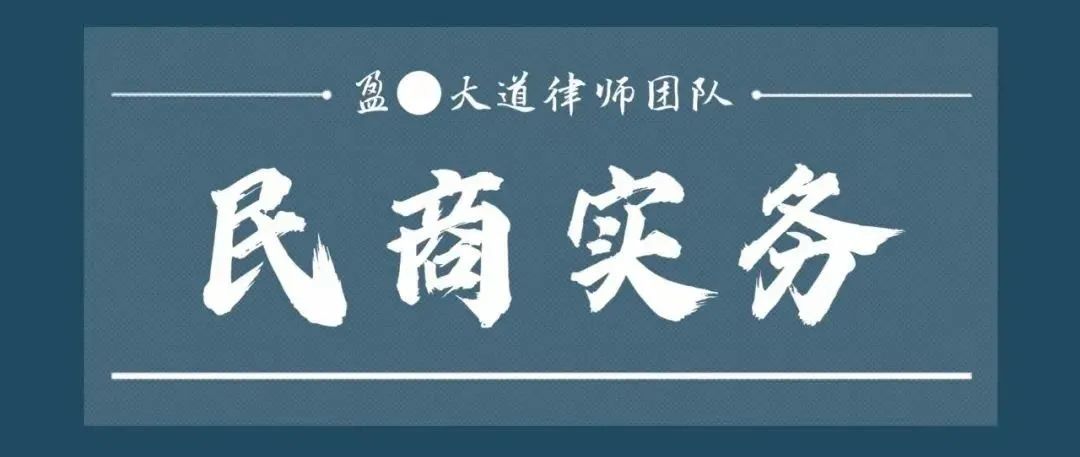《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增设了《公司登记》专章,规范了公司设立、变更、清算等环节的登记要求、程序和责任主体。2021 年 12 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下称“一审稿”)将公司章程首次纳入强制公示的范围,2022 年发布的二次审议稿(下称“二审稿”)又删除了要求公司通过统一的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文借此次《修订草案》关于章程公示相关规定的变动,尝试厘清章程公示相关理论与实务争议。
内幕交易犯罪行为必须是发生于内幕信息敏感期的交易行为,“内幕信息敏感期”是指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的期间。因此,判定交易是否构成内幕交易,需进一步对相关内幕信息的的形成时间和公开时间作出界定。
现行《公司法》 | | |
| 第六条第三款 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 第三十四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将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章程等信息通过统一的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将前款规定的公司登记事项通过统一的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
公司章程强制公示的争议:条文冲突、理论背景及实务顾虑
一方面,部分条文暗含了章程公示的内在要求,为章程的外部效力提供了文本基础。例如现行《公司法》及《修订草案》均有“章程另有规定除外”的表述,借由法律本身的公开性,第三人应当知道章程可能的排除效力,因此得出第三人具有合理审查章程的义务。在此前提下,将章程纳入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只是提供查询程序上的方便,不影响推定知悉的范围。另一方面,《修订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均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职权/董事会权力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这与《民法典》第六十一条“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相一致。依前文分析,若章程因公示产生对抗效力,则应推定相对人知悉章程对法定代表人职权/董事会权力的限制,在法定代表人越权签订协议等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善意,无所谓“善意相对人”,章程强制公示与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条款存在立法原意和适用上的冲突。章程是否应予公示,与公司章程的性质认定与对外效力密切相关,这也是学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例如关于章程的性质,学界主要有“契约说”和“自治法说”两种观点。契约说认为章程与股东协议没有本质区别,是公司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一系列协议。若采纳契约说理论,则支持章程外部效力的理由是相对人与公司签订契约时应考虑到公司一方的意思自治,而公司的意思表达正由这一系列协议的总体即章程代表,反对章程外部效力的理由主要基于合同相对性,认为章程作为协议不能约束不特定的第三人。相对的,自治法说认为章程既然对持反对意见的异议股东以及之后加入的股东也具有约束力而非如契约一般仅约束订立契约的当事人,理解为公司内部的自治法规更为恰当。若采纳自治法说理论,则支持章程外部效力的一面偏重于章程类法律规范的性质而认为其可以/应当与外部法律衔接,反对章程外部效力的一面偏重于“自治”的内部约束力而认为强制公示缺乏学理上的根据。关于将章程纳入公示系统,实务方面也有一些顾虑,例如关于章程是否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公示是否有泄露的风险的顾虑。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通常于证券交易所官网向公众披露,因此存在争议的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根据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其中(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及(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不属于公司登记事项,目前无需强制公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界定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及公司机构设置情况作为基本的经营信息,未达到“具有商业价值”的门槛,实际上无需在信息保护方面有所顾虑,至于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拟定章程时不必过于详尽,后续以协议等方式补充即可。
公司章程应予公示的法律效果:善意相对人及内外部关系
(一)缩小善意相对人的保护范围
法人登记的善意相对人指基于对公示的外部信息和表面特征的合理信赖作出决策的利益相对方。《民法典》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其本意为登记公示的公信效力,即善意相对人以登记事实对抗法人,将登记事实拟制为客观真实,并据此使相关法律事实发生相应法律后果的效力。根据反对解释,可依文义得出登记公示的对抗效力,即法人以登记事实对抗恶意第三人,推定其知悉登记事实的效力。关于“善意”的认定,有观点认为,公司章程如与登记事项公示地位相同,应具备同样的对抗效力,即推定合同相对方知悉,无法构成“善意”;亦有观点认为,“善意”要求的信赖应理解为对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具有全权代表法人这一抽象规则的信赖(一种系统信赖),因而相对人应否得到保护并不取决于其在与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是否尽到了调查义务。[1]2019 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 18 条围绕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问题,就此争议焦点作出详细阐释,认为债权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关联担保情形下对股东(大)会决议、非关联担保情形下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关联担保情形下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现行《公司法》第 16 条的规定,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被担保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但《九民纪要》也同时明确将债权人的义务限定于形式审查和必要的注意义务,避免过于严苛。依据该条款,在相对方具有调查义务的前提下,公司章程如纳入应予公示的范围,则应推定知悉。这样的制度设计缩小了善意相对人的保护范围,在争议解决中通常有利于公司一方。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自治规范,是公司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但多数观点认为并不能据此将公司章程仅视为内部治理规范甚至商业秘密而不具备对世效力。除登记事项外,《修订草案》一审稿第四十一条(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九十六条(现行《公司法》第八十一条)都规定了公司章程中应当载明机构职权和议事规则、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和变更办法等内部治理规范,全面公示将使公众和交易伙伴了解公司决策机制与程序,明晰公司对外投资、借贷、担保及关联交易等重大决策事项的适格决策机构,从而提高企业公信力,增强商业伙伴的交易信心,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商事流转的效率。此外,若与相对方产生纠纷,公司章程其实是与《公司法》具有同等地位与重要性的法律渊源,但因为涉及的章程条款无法查询,《公司法》规定由章程确立的制度经常被误解为管理性或倡导性规范。公司章程的公示将有利于这些制度落实为效力性规定,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填补内部治理与外部交易不同步造成的法律漏洞。[1]朱广新:《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制度中的善意相对人保护》,载《法治研究》2017 年第 3 期。
盈·大道律师团队是由盈科深圳律所刘晓安律师等领航,多名资深律师组建的一支一站式全方位法律服务团队。团队业务板块包括刑事诉讼与刑事风险防控、民商事诉讼仲裁与执行、常年法律顾问、房地产与建设工程、投融并购与资产证券化等。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与鹏程一路广电金融中心 32 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