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3届兰花博览会
“银都鹤庆・兰韵幽芳”
主题艺术大赛
文学获奖作品展播
优秀奖
兰露记
李成裕
鹤庆的雾是有重量的。
寅时刚过,青石板路上的露水已经能洇透布鞋。我跟着老张往兰园走,他的竹杖敲在地上,惊起几片蜷在草叶上的雾,像揉碎的棉絮,又落回那些半开的兰花苞上。“兰草喝露水,跟银匠淬火一个理,”老张回头看我,杖头在晨光里泛着淡青,“少了这道工序,香里就缺三分骨。”
兰园在鹤庆坝子边缘,三十亩地围着半人高的石墙,墙头上爬满三角梅,此刻倒成了雾的栅栏,把那些白的、紫的兰草气息圈在里面。老张管这片园子叫“三露堂”,他说自己这辈子就认三样东西:朝露、夜露,还有兰草叶尖那滴不肯轻易落下的露。
一
老张的兰园里,最老的是那株大雪素。
它长在东墙根的紫砂盆里,盆沿缺了个角,据说是民国年间一个银匠失手磕的。我第一次见它时,正赶上抽箭,六片叶子斜斜地舒展开,像被谁用指尖捋过,每道叶脉都绷得笔直。“这草,比我岁数大,”老张蹲在盆边,指尖悬在叶尖上方半寸,不敢碰,“当年我爹从山里挖它回来,用的是装银子的木盒,垫着红绸子。”
那是1958年的事。老张说,那年他才八岁,跟着爹往老君山深处走,走了七天七夜,干粮吃完了就嚼树皮。“你爷爷——就是当年县上的银匠头儿,”他忽然改了称呼,我这才想起,他总把我当故人的孙辈,“他跟我爹说,老君山背阴处有兰草,开得像刚錾好的银花。”
他们找到兰草时,正赶上一场山雨。老张的爹脱下褂子裹住花盆,自己淋得直打哆嗦,下山时摔在石崖上,腿骨裂了,却死死把花盆护在怀里。“后来他躺了三个月,”老张的竹杖在地上画着圈,每天让我用小勺舀山泉水喂它,说这草沾了人气,将来开的花能治病。
我后来在县档案馆见过老张爹的照片,穿件洗得发白的对襟褂子,怀里抱着个花盆,背景是老君山的云。照片边角已经泛黄,但能看清他左手腕上的银镯子,上面錾着兰草纹——那是老张母亲的陪嫁,据说后来当了,换了粮票给兰草买肥料。
二
兰园西头有片地,种着“剑阳蝶”。
这种兰草的花瓣上有紫斑,像谁不小心滴了墨,又晕开几缕。老张说,最好的“剑阳蝶”,斑要像银匠点上去的焊药,浓淡得恰到好处。“去年有株草,斑长歪了”,他指着空着的畦垄,“我把它挖了,埋在梅树下,给别的草当肥。”
他对兰草的苛责,像银匠对成色的挑剔。我见过他给兰草分盆,用的是一把磨得发亮的铜刀,刀刃薄得能映出人影。“分根就像分银子,”他眯着眼量根须的长短,“多一分浪费,少一分活不成。”那些剪下的残根,他从不扔,说是埋在土里能养地气,来年别处的兰草会开得更旺。
有年春寒,园里的“剑阳蝶”全打了蔫。老张在园子里支起十几口铁锅,烧松针熏气,自己裹着棉被守了三夜。后半夜最冷的时候,他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在他脸上跳,“我听见草叶响,像有人在跟我说话,说再熬半个时辰,天就亮了。”
天亮时,他发现最靠边的那株“剑阳蝶”,竟顶破冻土抽出个花苞。现在那株草还在,叶片上有道浅浅的黄痕,据说是那晚冻的。老张常对着它出神,说这草有性子,跟当年那个不肯涨价的银匠一样,认死理。
三
兰园的竹屋里,摆着个旧木柜,锁是银做的,上面錾着兰草。
老张打开锁时,我听见咔嗒一声,像时光松了扣。柜子里没有金银,只有几十本账簿,纸页黄得发脆。他翻到1983年那本,指着其中一页:“这天,你爷爷来买兰草,说要送给省里来的人。”
那年鹤庆刚恢复银器交易,老张的爹已经过世,园子里的兰草快被人挖光了。你爷爷背着个布包,里面是他刚錾好的银镯子,老张的指尖在“三两六钱”那行字上停住,“他说用镯子抵兰草钱,我说不行,他就蹲在门槛上,跟我讲了一上午银匠的规矩。”
银匠的规矩里,有一条是见好就收。比如打银锁,分量够了就停,多一分是贪心;比如錾花纹,线条到了就止,多一笔是画蛇添足。“兰草也一样,”老张合上账簿,“该浇水时浇水,该晒太阳时晒太阳,急不得。”
后来那株“小雪素”,被你爷爷摆在银铺的柜台里,据说来买银器的人,总先被花香勾住脚。有次省里的人来视察,见了兰草,说这才是鹤庆的魂——既有银的硬气,又有兰的柔肠。“那天你爷爷喝醉了,”老张往灶里添了把柴,“他说,银匠敲打的是日子,兰草开的是念想。”
四
每年兰博会前,老张都要选一盆“当家花”。
今年他选的是株“绿云”,花瓣带着翡翠的润,叶尖却微微泛红。“这草,根扎得深,”他用竹片拨开培土,我看见那些根须在土里盘成个圈,像只攥紧的拳头,“就像鹤庆的银匠,看着软,骨头硬。”
他给这株草换盆时,特意用了个新錾的银盆,盆底钻了七个小孔。“银盆透气,”他解释道,“就像人得喘气,草也得有念想。”换盆那天,园子里来了群年轻人,扛着摄像机,说要拍“兰草与银器”的纪录片。
老张不喜欢镜头,却喜欢听年轻人讲外面的事。当听说现在的银匠能用电脑设计花纹时,他没生气,只是笑:“工具变了,规矩不能变。就像兰草,换了花盆,根还得扎在土里。”
拍摄间隙,有个戴眼镜的姑娘问:“张大爷,您守着这园子,不觉得闷吗?”老张指着那株“绿云”,花瓣上的露水正往下滴,落在银盆上,叮的一声。“你听,”他说,“这声音,比城里的喇叭好听。”
五
兰博会开幕那天,老张请了个老银匠。
老银匠姓寸,今年八十岁,手抖得厉害,却坚持要给“绿云”的花盆錾上兰草纹。他的工具摊在红布上,小锤、錾子、锉刀,摆得像列队的士兵。“年轻时,我跟你爷爷比过手艺,”寸大爷眯着眼,把錾子对准银盆,“他说我錾的兰草,叶尖少了点灵气。”
小锤敲在錾子上,当当的声响在展厅里散开,像谁在敲醒沉睡的时光。围观的人都屏住呼吸,看着那些兰草叶一点点在银盆上生长,叶尖的弧度,正好接住从天窗漏下的阳光。“好了,”寸大爷放下锤,额头上的汗珠掉进银盆,“这道弯,是学你爷爷的。”
老张把“绿云”摆在展厅中央,周围是他选的二十盆兰草,每盆都配着银器——有的是银托架,有的是银铭牌,最显眼的是那盆“大雪素”,花盆外裹着圈银网,网眼细得能接住露水。“银护着兰,兰养着银,”老张对围观的人说,“就像鹤庆人,守着手艺,也守着念想。”
那天傍晚,我看见老张坐在展厅门口,竹杖斜靠在腿边,手里攥着片兰草叶。叶尖的露水终于落下,砸在他的布鞋上,洇出个小小的湿痕。“你爷爷说过,”他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雾,“兰草的香,是鹤庆的魂在喘气。”
六
离开展会前,老张给了我一株兰草。
他说这是今年新收的,让我带回城里,种在阳台上。“不用天天浇水,”他叮嘱道,“隔三岔五看看就行,草跟人一样,得有自己的心思。”
回来后,我把兰草种在个旧陶罐里,那是母亲留下的,罐口有圈兰草纹。三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看见土里冒出片新嫩芽,嫩得像玻璃,叶尖挑着滴露水。阳光照在上面,竟映出点银亮,像谁不小心把鹤庆的晨光,落在了我的窗台上。
此刻我忽然想起老张的话,他说兰草的露,其实是大地的念想,不肯轻易落下,是怕人忘了那些扎根的日子。就像鹤庆的银匠,一锤一錾,不是在打银器,是在给时光刻上念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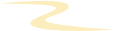
作者:李成裕
编辑:唐忠宇
审核:杨 帆
终审:唐 伟
法律顾问:奚金才



转载请注明来自“鹤庆融媒”微信公众号。
投稿邮箱:hqrongmei@163.com
?点击关注“鹤庆融媒”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