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十月的风里已经有了凉意.

我站在会展中心外面的长堤上,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像极了我此刻的心绪.
手里攥着一颗大白兔奶糖,那是刚才在便利店随手抓的,包装纸被捏得皱巴巴的,发出细碎的声响.
远处金门的灯火若隐若现,像是一把撒在海面上的碎钻,又像是谁遗落在时间缝隙里的眼泪.
我想起张爱玲说,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此刻我觉得,生活更像是一颗放得太久的糖,剥开来,表面已经化了一层,黏糊糊的,粘手,却又舍不得扔.
这几年,我像个没有脚的鸟,从上海的梧桐树下飞到香港的中环,又在纽约的第五大道迷失过方向.
那时候总觉得,只要跑得够快,孤独就追不上我.
可现在,站在这片陌生的海边,看着对岸那点微弱的光,忽然明白,孤独不是影子,它是骨头里的磷,只有在黑夜里才会发光.
会展中心的灯光突然全亮了,巨大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芒,把周围的一切都照得透亮.
这种亮度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好像是被扒光了站在舞台中央,所有的不安、焦虑、甚至是那些隐秘的渴望,都无处遁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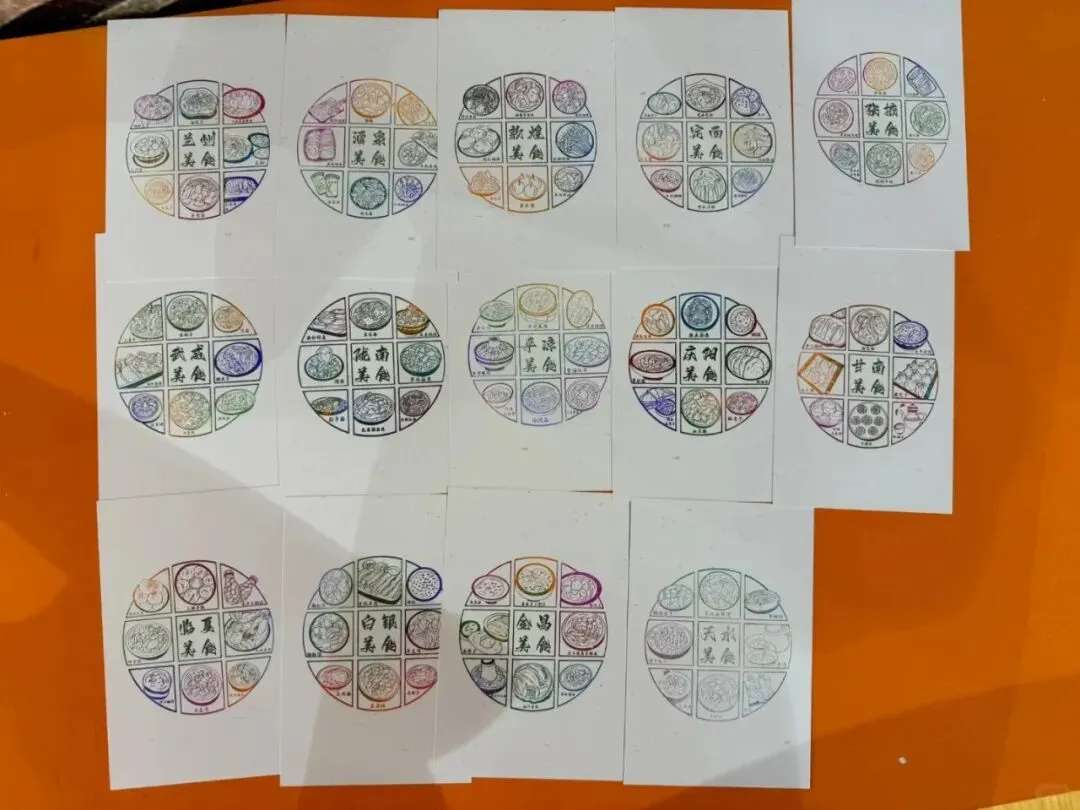
我下意识地把那颗糖剥开,塞进嘴里.
甜腻的味道瞬间在口腔里炸开,带着一股廉价的奶精味,却意外地让人安心.
小时候在弄堂里,外婆也是这样,在我摔倒哭鼻子的时候,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塞进我嘴里,说:“吃颗糖就不疼了.”
那时候的疼,是真的疼,膝盖破了皮,渗出血珠.
现在的疼,是看不见的,像是有人拿钝刀子在心口慢慢地磨,不见血,却让人喘不过气来.
海浪拍打着堤岸,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又一下,像是某种古老的节拍.
我想起在香港的那几年,住在狭小的公寓里,窗外是密密麻麻的楼房,连天空都被切割成一个个方块.
那时候我也常听海,维多利亚港的海水总是带着一股机油味,忙碌,喧嚣,充满了欲望的味道.
而这里的海,似乎更沉静一些,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淡然.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有些变形,像是一个被拉扯的灵魂.

旁边走过一对情侣,女孩手里拿着一串气球,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那种毫无杂质的快乐,我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过了.
或许,我们都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在这个巨大的、流动的城市里,试图抓住一点什么.
就像这颗糖,明明知道吃多了会蛀牙,明明知道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那一瞬间的甜,就是救赎.
我蹲下来,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扔向海里.
石头沉入水中,甚至没有激起什么浪花,就像我的那些过往,扔进时间的洪流里,连个响声都没有.
突然想起在纽约的那个冬天,大雪封门,我一个人在公寓里读伍尔夫,她说:“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那时候不懂,以为成为自己就是要去远方,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现在才明白,成为自己,或许只是在这样一个平淡的夜晚,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孤独,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
海风越来越大了,吹得脸有些生疼.

嘴里的糖已经化完了,只留下一丝淡淡的甜味.
我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
远处的灯光依然亮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又像是在送别着什么.
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吧,一边失去,一边寻找,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用一点点甜,去对抗漫长的苦.
我裹紧了风衣,转身走向路边的灯火阑珊处.
那里有一家小酒馆,我想去喝一杯,敬这无处安放的孤独,也敬这温柔的夜色.
或许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依然是那个在城市间穿梭的过客.
但至少今晚,在这片海边,我短暂地拥有了自己.
这就够了,真的.

